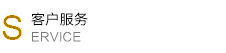家鄉溫暖我一生的熱炕
熱炕需要每天填炕,因此也成為母親每早的必做功課。記憶中每天早晨起床的母親身上總是有一些炕灰、草屑,或者干糞末。那干糞是燒炕最好的燃料,用木柴太烈,也用不起;用干草太不耐燒,只有那曬干后很末的糞才能燒出溫熱適中的熱炕。
那種混合著青草和別的什么的氣味是我所熟悉的。
我在城市多年,一早已背叛了鄉村,那種氣味也離我遠去。但我對家里的那兩面大炕記憶猶新.那溫熱的感覺刻骨銘心。那一年我上小學,回家的路上和幾個同學鬧著玩,不小心掉到河里,渾身結滿了冰塊塊,母親一邊嘮叨一邊把我脫得精光,一把塞進熱被窩里,我精光的小身體幾乎要融化在一股溫暖中。三十幾年后我仍喋喋不休地向我的孩子們講這事。他們既不好奇,也不覺得有意思。他們常常把話題引到馬拉多納或是國家隊的某個臭腳上去。
一股暖流在某一個冬天溢暖了一個人的全身,但那與別人又有什么相干呢?你盡可以在這股溫暖的回味中生活半生或一生,那是你自己的事。有些事用語言表達出來是徒勞的.其實你根本用不著訴說,這種用身體感覺之后的幾十年中仍留存在內心的事,根本就是你自己的事,別人無法體會,也無法與你分享。
也就是從那一次.我牢牢記住了溫暖的土炕。
另外一件事是,因為我離開了土炕.從此就有了一股寒氣侵人我的生命。
也是某一個冬天,我離開了家。當時我根本沒有意識到,離開家就意味著離開每天由母親燒熱的那面大炕。當時的這個行動徹底地改變了我生活的方向,我不清楚那溫暖的上炕對于我該有多重要。母親在幫我收拾行李時,特意準備好了一張厚厚的羊皮讓我帶上。我說.這根本用不著,再說也太累贊。母親卻說.我知道你們是睡在那木板床上,沒有燒炕。沒有燒炕要過一個冬天,孩子,你會覺著冷的。 我沒有聽母親的話,把一套單薄的被褥鋪在板床上。慢慢的,在漫長的冬夜里我開蛤感覺到了冷.我把身休彎曲成一張弓。
我失去了一面炕.得到了一張床。我的生命在度過那個冬天時差不多擱淺了。
我常常抱著那個并不怎么旺的火爐子,火爐子烤熱了我的前心.卻把我的后背晾在了另一面。那扇松松垮垮的破門扇上糊上去的舊報紙,常常被調皮的學生川尖利的指甲劃破,那些劃破的裂縫用來滿足他們的好奇心。寒風也有著和孩子們一樣的脾氣,偷偷從門縫中刮進來,然后吹到我的后背上,一股寒氣從后背上彌漫開來。從那時開始,我的后背就再沒有熱過.不管我怎么轉過身,背朝著爐子烘烤,但只要轉過身來,那脊背就寒氣入骨。
在此后的歲月里這個毛病一直保留了下來。人生中許多的事情讓人捉摸不透.有些事是你刻意追求的,它始終無法實現,而有些事悄你不留意就一下子刻人你的骨髓,進人你的生命中。像冬天我冰冷的后背,就在每一個寒風刺骨的日子里告訴我,人生有許多的不經憊.比如數年前的我要是不離開母親,我年輕的身體在寒氣襲人的冬日很舒服地烙在那面大炕上.我的一生都將很溫暖。